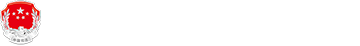防护栏与救护车
来源:守法普法协调小组2023-09-20
近年来,法院平反了几起实打实的冤案。湖北的佘祥林、河南的赵作海、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、河北的聂树斌,他们的冤情之浮出水面,或者源于“亡者归来”,或者基于“真凶现身”。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能理解“无妄之灾”一词含义的人。这些案件虽然情形各异,但其原因都有相似之处。呼格和聂树斌早已被执行死刑,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被定罪前曾发生过什么,而侥幸活下来的佘祥林、赵作海,则无一例外地讲述了他们曾遭刑讯逼供的经历。一个人只有在“痛不欲生,但求一死”的情况下,才会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,因此,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曾遭受过怎样的非人待遇。
小时候看关汉卿的《感天动地窦娥冤》,知道给窦娥上夹棍、打板子都是在演戏,是假的,自然也就无甚感想。现在回看该剧,则明白了屈打成招的具体样式。“真凶”张驴儿知道在官衙里会有拷打,“你这等瘦弱身子,当不过拷打,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!”他以“官休”还是“私休”来要挟窦娥,而糊涂的楚州太守只知道“人是贱虫,不打不招”,审断方法只有“左右,与我选大棍子打着”这一招。再读到“没来由犯王法,不提防遭刑宪,叫声屈动地惊天!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,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”“有日月朝暮悬,有鬼神掌着生死权,天地也,只合把清浊分辨,可怎生糊突了盗跖、颜渊?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,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。天地也,做得个怕硬欺软,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。地也,你不分好歹何为地?天也,你错勘贤愚枉做天!哎,只落得两泪涟涟”这样的戏词时,才能理解该剧的震撼之处——个人在面临强大而合法的公权力的暴力时,她的屈从中隐含的是深深的无助与绝望。现实生活中侥幸活下来的人曾说他们一直相信法律会还他们以公正,而呼格和聂树斌在身赴刑场时,不知是否也曾有过窦娥这种“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”的憾恨?
其实,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刑讯会导致冤案的发生。早在西汉时期,司法官路温舒就曾上书宣帝要“尚德缓刑”。他说,“夫人情安则乐生,痛则思死,棰楚之下,何求而不得?故囚人不胜痛,则饰辞以视(示)之,吏治者利其然,则指导以明之,上奏畏却,则锻练而周内(纳)之;盖奏当之成,虽咎繇听之,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?成练者众,文致之罪明也”。按照人之常情,平安时就愿意活,痛苦时则宁可死,在严刑拷打之下,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呢!于是,逼供、诱供就会收到明显的成效,而由于屈打成招、罗织构陷的罪行也更显周密而自洽,可织造出“完整的证据链”,所以,即便是法祖咎繇在世,也会认为犯人是死有余辜的。
尽管人们早有这样的认识,但由于古代侦破技术有限,加之犯人的口供乃“证据之王”,所以历朝历代并不禁止刑讯,最多在开明的朝代里对刑讯做一些限制。于是,当比我们早一步“走出中世纪”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后,最先观察到的就是公堂上刑讯的不堪。曾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,在他的《中国总论》中,就曾对此进行过详细的介绍。他说,虽然律例中描述了合法的刑具,包括三块板上挖大小恰好的槽用以压脚踝,五根圆棍用以压手指,也可以加上竹板(拶指),但在拷问中用其他方法的事是常有的。
直到清末实施新政期间,修律大臣沈家本、伍廷芳在《奏停止刑讯请加详慎折》后,仍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。后者认为,如果罪犯有罪证据太少,而且又拼死抵赖,那么,不用刑讯就难以结案,也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。当然,晚清政府的这一举措还是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。1908年,年仅十七岁的胡适就在《竞业旬报》上发表了《停止刑讯》的短评,“我们中国讯官司的时候,专用各种刑法,屈打成招,往往有之。所谓三木之下,何求不得也?要晓得这用刑讯一事,是文明各国所没有的,所以前年便有上谕,要停止刑罚,如今法部又行文到给各省的地方官,一律停止刑讯。唉……只是太便宜了那班大盗老贼了”。这最后一句的感叹,倒也反映了民众的一般心理。
不消说,从清末发展至今,刑讯逼供早已失去了它的合法性,甚至还将刑讯逼供入刑。然而,实施效果并不理想,现实生活中因此而致伤致死的案件时有发生。近年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,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刑讯逼供现象,由此而造成的冤错案还是会时不时见诸报端。为聂树斌等人的冤案平反固然给人以“正义从不缺席”的慰藉,却免不了死者不能复生的遗憾。毕竟,与其事后昭雪,莫如事前的预防——与其在谷底准备一辆救护车,不如在悬崖边安装防护栏。这或许是呼格、聂树斌等人用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的道理。
(文章节选自马建红《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)
(稿件来源:法治日报、中国普法网)